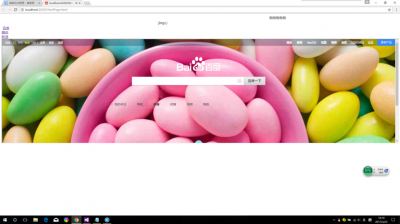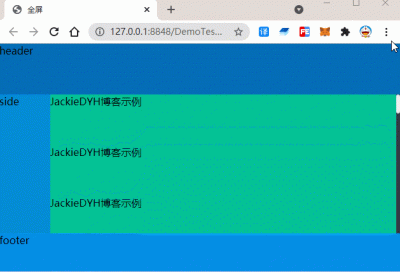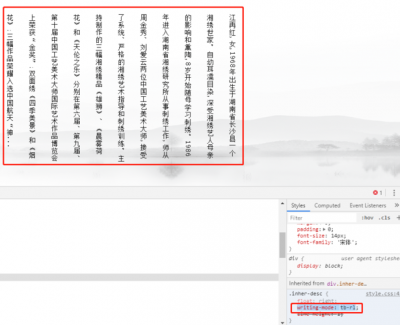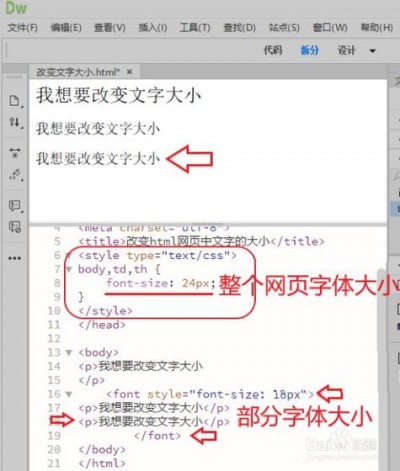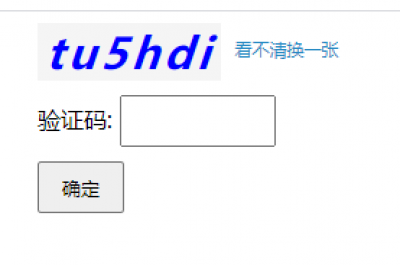来源:神经现实
摘要 / Abstract
大脑如何演化为如今的复杂系统,它的未来又将走向何处?大脑的存在对现存的理论提出了这样一个挑战——我们都知道,熵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可避免的增长,它常常与无序性及简单性(译者注:该简单性在概念上与下文中的复杂性相对)联系起来。近来我们展示了演化是熵值演变的过程:结构的建立(即生命的产生)促进了熵增。在这里,我们提出,演化的关键跃迁点与生命对于时间及空间的操纵相关,经由复杂的多维度状态空间(multi-dimensional state space),生命打开了促进熵增的新通路。大脑的演化促成了时间和空间在大脑中的表征,而这种表征又进一步加速了熵增的过程。然而,这些通路有时指向了状态空间中的死胡同,因此根据热力学定律,我们无法预测复杂的生命系统将在未来持续存在。
复杂系统演化之谜
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出现了两个意义深远但看似相互矛盾的理论,这两个理论重塑了我们对于宇宙的理解及我们在宇宙中所处位置的认知。第一个理论是热力学第二定律,该理论认为宇宙朝着熵增的方向发展;另一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两个理论都有着数据支撑,但对宇宙的走向提出了截然不同的预测:熵增将导致整个体系朝着混乱与无序发展,而近四十亿年的演化提升了人类社会的秩序与复杂性,并带来了今日结构复杂的人类文明。为什么同样由数据驱动的理论在解释宇宙发展时走向了无序与秩序两种结果?
近来,我们探究了时间及空间结构在这两种结论中架设桥梁的可能性。具体来谈,我们想知道生命是如何掌握在保证自身存活几率最大化的前提下进行致使熵增的化学反应的。生命找到了一条将引导熵值穿越多维度状态空间(multidimensional state-space)迷雾的新通路,由此在熵增的同时达到了更有序的复杂状态。在这里,我们将上述问题的对象外延至大脑,即大脑在提升可达到的状态空间大小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后文中,我们将着重讨论上述过程中大脑在时空表征上的演化,并对这种演化在未来的发展作出推测。
熵
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熵是与自由能(free energy,即对外做功的能量)相对的概念。熵值总是增加,就如同进入一系列相连容器的气体总会找到斜率最高、直径最宽的通道从而以最快的速率上升。与之同理,随着时间流逝,系统总会从可能性低向可能性高的状态变化——基于玻尔兹曼(Boltzmann)的理论,可能性较高的状态指的是能够被数量更多的微观结构(microscopic configurations)所实现的状态。一旦系统达到热力学平衡态即最大熵值状态,该系统将不会再做功,也不会再发生任何改变了。
熵与空间同质性及梯度损失相关。举个例子,熵值随着物质自发的均匀分布(如两种起初分离的气体相互混合)而增加。与之相似,热量随着温度梯度(temperature gradient)降低也带来了熵增,这是由粒子热能在空间上的均匀分布产生的。空间中自由活动的粒子最终总是呈现出无结构的随机排布,这种现象的本质原因很简单——无序状态比有序状态有更多种可能性。玻尔兹曼将熵量化为能够保持宏观态的微观态数量:对于空间结构有序的系统,如容器中的气体或寒冷/温热的物体,能够保证系统状态(宏观态)不变的粒子排布(微观态)方式较少,因此该系统的熵较低。
然而,熵增并不总是带来无序的空间排布,有时系统中的熵增反而会降低空间一致性。例如,当我们把油倒进水中时,油与水会自动分层。分层后该系统的空间排布变得更加有序,但其熵值变高。这是由于在重力的作用下,水分子的因重力作用所产生的运动与油滴向上的作用力相互抵消,从而释放了能量并促进温度上升:尽管粒子可活动的(总)空间变小了,但每个粒子的活动速度变大了,也即系统内可能的微观态变多了。由此可见,熵并不只与宏观上的有序/无序相关,熵与系统中的可能性联系更为紧密:随着时间推移,系统将不断朝着充满更多可能性的宏观状态推移。对于诸如行星、星系抑或是生命本身的系统而言,结构化的状态可能带来相比混乱状态更多的可能性。
熵的增长并不是连续不断的:系统可能短时间内稳定停留在熵值较低(自由能较高)的状态。我们可以把这种短暂的中间态设想成抽象时空中的气泡——一棵生长数年的树在被雷电击中之前保持着稳定的低熵值状态,直到这场闪电带来的大火将其毁灭。在毁灭的刹那,大树所存在系统的熵值瞬间增高。在这个例子中,雷电通过毁灭树木把压制在抽象气泡中的熵瞬间导入另一个更大的气泡中。因此,一棵树的存在不是持续不变的,我们将这种状态称为亚稳态(metastable)。
生命与熵
接下来我们将要探讨生命,以及为什么生命演化成为如今的复杂形态。薛定谔(Schrödinger)认为生命的发展是对环境熵值的逆转。为了维持生命的低熵值,生命需要对其生存环境进行熵增改造。这个观点背后的预设是,能够成为生命的结构必然需要低熵值。然而,根据上述讨论,我们认为生命也可能是与油水混合物、聚变星或是黑洞相类似的系统——一个本身具有高熵值的系统。基于物理学定律及宇宙的现状,生命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它为整个体系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生命的结构与秩序并不意味着它将降低系统的熵值,就如我们之前所讨论的,在某些进程中,在产生秩序的系统中也可能引起熵增。
演化跃迁,复杂性与时空
演化跃迁(功能上的步骤性改变)是演化的显著特征之一。Szathmary 及 Maynard Smith 提出,在演化进程中出现过数次较为重要的跃迁。在这里,我们将着重讨论一系列促成时空交互的跃迁点。
随着能自组装(self-assembly)的碳基分子及能够复制自身序列的核酸的出现,生命出现了。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演化成为了一往无前的车轮,在前行过程中,有利于自我复制的新分子被得以保存。碳原子四面体排列的空间结构使得它能够形成稳定的聚合体长链,从而保证了自我复制的机制得以留存。此外,这些分子的灵活性使得底物在空间上能够紧密接触,进而保证了新化学反应的进行:化学反应将自由能转换为热量,提升整个系统的熵。综上,碳基在空间的维度上通过化学反应促进了演化,而核酸通过自我复制在时间维度促进了演化。
演化接下来的进程进一步为生命提供了通过化学反应操纵时空的能力。随着膜结构及细胞的出现,化学物质被“隔室化(compartmentalised)”,化学反应因而得以在不受外部环境干扰的前提下进行。该演化极大地促进了化学反应的效率及稳定性。三磷酸腺苷(ATP)也随着演化出现于生命早期。ATP 使得生命在不受时空条件所限的前提下利用储备的能量进行化学反应,该演化同样保障了生命稳定性及自我复制性。通过捕捉、储存当下的能量,令其在未来能为细胞所用,ATP 在时间维度上促进了演化,而通过在细胞内搬运能量,第二信使(second-messenger)*系统在空间上促进了演化。35 亿年前,光合作用的出现又促进了上述反应:自此,细胞得以捕获并储存来自太阳的大量能量。
*译者注
第二信使:胞内信号分子,负责在细胞内进行信号传导从而触发如增殖、细胞分化、迁移、存活及细胞凋亡等生理变化。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cond_messenger_system]
接下来,细胞内部演化发展出了新的时空操纵方式。26 亿年前,细胞中演化出了电压(voltage)、配体门控(ligand-gated)离子通道、受体激酶-转录因子信号通路及调控基因表达的能力。此外,细胞基于微管*搭建出了胞内运输系统,该系统保证了细胞内部的分子能够在合适的空间与时间点上参与反应。这些胞内系统进一步组成鞭毛(flagella),于是细胞具备了自由活动的能力。细胞的运动进一步加强了生命的稳定性、促进了生命的自我复制。此外,运动让细胞具有了与其他细胞接触并交换基因的能力。通过基因交流或有性生殖为基因序列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从而开启了新的熵通道。
*译者注
微管是细胞骨架的组成部分。它遍布于细胞质中,负责维持细胞结构及胞内物质的运输。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Microtubule]
演化带来的细胞间交流表现出了显著的适应性优势,于是,多细胞生物诞生了。起初出现的多细胞生物(如现代海绵)形态单一,随后出现了具有形态差异的生命。这些差异可能体现在空间上,如功能不同的器官;也可能体现在时间上,如随着生命的生长发生的变化差异。这些功能性差异的结构性基础是基因组之间的交互影响。
在此基础上,诸如同源异形框基因(homeobox genes)不仅能够编码蛋白,还能通过基因间的相互调节创造出规模较大的空间结构,同时为生命的发展提供秩序。
在大约 5 亿到 6 亿年前,一类新的细胞出现了。这些细胞具有电兴奋性(electrically excitable),该特征不仅保证了信息能够快速的在细胞间传播,且确保了信息由细胞内至细胞外的传输——这些细胞是第一批神经元,神经元的出现保证了生命对时空的进一步操控:它们给予了生命在环境中运动的能力和表征时空的能力。
运动
在六亿年前,地球上仅仅充斥着水生生物。他们要么无法运动,要么凭着洋流移动。生命的静止持续到了大约五亿六千万年前,直到能够自主活动的多细胞生命以蠕虫类生物的样貌出现。起初这些生物只能在海底有机矿泥中径直穿行,随后,它们又进化出了转弯和挖掘的能力——海床化石中的蜿蜒甬道为它们的这些行为提供了证据。这种进化的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自此之后,生命不再被动等待——它们掌握了主动获取自由能的力量。
约五亿四千万年前,地球上的生命迎来了长达一千三百到两千五百万年寒武纪大爆发(Cambrian explosion)。现今存在的绝大多数生物门类都在这一时期出现,直到今天我们无法解释是什么导致了随寒武纪大爆发出现的井喷式的生物多样化。这一现象可能是由神经元及肌细胞的出现催生的:神经元和肌细胞给予了生命自由活动及快速处理信息的能力,这可能助推了新生命(即抽象状态空间中的气泡)的产生。
运动的演化增加了系统的选择压力(selection pressure),还促进了捕食行为的增长——生命不再被动地通过光合作用或是清理残骸上的有机物来获取能量,运动给予了生命追逐和捕食的能力。寒武纪期间的生命演化出了外骨骼,这让我们有机会通过化石证据一睹远古时期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斗争。与此同时,复杂器官的出现又促进了动物的觅食,捕猎及逃脱等行为。以演化的时间观来看,生命复杂器官系统的发展非常迅速:从近来科学家们发现的一块五亿两千万年前的节肢动物(arthropod Fuxianhuia protensa)化石中我们能够看到,完整的视觉系统、大脑及视叶已经出现了。
空间、时间和记忆
因为世界同步靠的是时间,所以储存关于过去的信息能力使生物能对未来做出预测——这对生存来说有着极大的作用。因此,神经元的出现伴随着突触可塑性,神经网络过去的活动因此得以被保留下来,这也许是绝大多数,甚至全部形式的记忆的神经机制。突触可塑性的演化可能与核酸的演化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两者都允许当前的状态被跨越时间地储存下来——这就允许生物利用过去的信息来预测(并利用)未来。
记忆的一项重要用途,就是储存空间信息。一旦动物开始远距离移动,一个新的选择压力就会逐渐明显:环境中的一些区域,会比另一些区域有更高的生存潜力(survival potential)。如果一个生物能通过储存通往高潜力区域的导航信息,来利用这种生存潜力的不同,那将会对这个生物的生存形成极大的优势——于是,内在的空间表征就诞生了。目前,我们尚不清楚这种能力是如何在早期的运动动物中发展出来的,但我们能通过有限的化石记录,和地球上现存的各种神经空间系统,来进行合理的推测。
最原始的导航系统,灯塔导航(beacon navigation),只需要动物探测到一个合适的环境目标并向之移动。这种探测能力可以是与生俱来的,例如昆虫朝着光亮移动;但这种能力也能从经验中习得。更复杂的空间表征则不仅需要自我中心编码(egocentric coding,编码外界物体相对于自己身体的位置),还需要非自我中心编码(allocentric coding,编码外界物体在世界中的客观位置)。一个使用非自我中心导航系统的生物,需要表征移动的方向(direction)和距离(distance),从而建立一个外界空间的二维模型。
方向感是一个古老的能力,早在脊椎动物出现之前就已出现:早至昆虫,晚至哺乳动物,大家所使用的神经“罗盘”在重要方面上并无二致。但与此同时,动物也需要监测自己的移动距离,并将移动距离与移动方向用三角学方法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准确地回到旅途的起点。包括昆虫在内的各种动物都具有这种“路径整合”(path integration)的能力。路径整合的演化允许运动动物建立起可返回的营地,这对生物的生存至关重要,这促进了自我复制和延续,也因此打开了通往更多状态空间泡泡的通道。
与此同时,路径整合也允许生物以非自我中心的方式,表征外部世界中有显著特征的地点。这些地点可以被进一步整合,形成与地图类似的内在表征,这允许动物对它们所处的环境建立细节丰富的模型。海马体(hippocampus)通过接收(和处理)方向、距离、环境中的物体和事件信息,成为了哺乳动物实现路径整合的关键。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海马体也能表征时间。对于一个运动的动物来说,时间和空间本身就在速度和距离的计算中被整合了,但时间或许也能被独立地表征。对时间的表征能增强空间记忆的预测能力。比如,具有时间概念的动物能知道它们有一段时间没探索一个特定的地点了,因此也许需要重新探索一下那个地点;或者,它们能知道猎食动物什么时候经过一片海滩,从而预测海滩在什么时候会变得相对安全。对人类来说,同时表征空间和时间的能力允许我们形成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也就是对生活事件的记忆;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对尚未发生的事情和不会发生的事情分别进行计划(planning)和想象(imagination)。
人类
由此,人类和他们复杂的活动形式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在很多方面上,人类与其它亿万个物种别无二致。但是,人类似乎是现存物种中,唯一能使用符号语言的。语言不留下任何化石痕迹,我们因而无法确定人类语言出现的具体时间——但这肯定比人类与大猩猩分道扬镳要晚上几百万年,而且很可能与人族(hominin)大脑的体积在过去三四百万年间的飞速增长紧密相关。语言的产生和上面提到的其它认知能力(例如我们复杂的情景记忆)可能是并肩演化出来的。
在本文的讨论中,语言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允许我们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一个个体到另一个/多个个体,从一代个体到下一代个体)来储存和传递信息。如同其他的演化转折一样,语言的出现让人类能够探索相空间*内更多的区域。个体的想法被时间和空间分隔,要想集中力量办大事,人类需要可以汇集个体想法的能力,而语言恰好提供了这种能力——语言之于认知,就如同生命初始的分子对接之于生命本身。
*译者注
相空间:即 phase space,用来表达一个系统能处在的所有状态的空间;在一个系统的相空间内,这个系统所有可能的状态都有其对应的点。
多亏语言,人类得以探索物理(例如对星球和外太空的探索)和抽象(例如对抽象领域,如数学、艺术、科学和哲学等的探索)的空间。这致使原先不会相互作用的系统之间,发展出了相互作用,并对生态圈(ecosphere)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举个例子,人类将数量庞大的植物和动物物种,从一个大陆上搬运到了另一个大陆上,导致了许多物种灭绝和疾病的自发性传播——近期的人畜共患传染病 COVID-19 就是一个相关例子。在新型冠状病毒突变之后就发生了航空传播,让病毒得以散布到了全世界,而如今,它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各种环球系统,从货物流,到人群流动,再到各个经济体的运作。另一个例子,就是在工业革命后,人类对地下化石燃料储蓄的开采。这已经影响到了整个地球的气候系统,留下了需要用地质学时长术语来描述的长远改变;我们有了描述人类时代的地质学名称——人类世(Anthropocene)。
光是由语言衍生出的科技本身就在快速地更新换代。过去的一百年间,我们见证了电子信息革命,其影响之深远甚至超过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与能量相关,电子革命与信息相关,两者都与熵密不可分,两者都致使大量的熵流入它们产生的“泡泡”中。我们目前正在接近一个新的技术演化点,那就是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发展——在不远的将来,人工智能将允许独立于人类的、新的智能存在。毫无疑问,这会在我们与相空间内的许多新泡泡之间搭建连接。人类要拭目以待的是,这些新的泡泡中,有没有哪一个泡泡象征着人类的灭绝。
结语与展望
最后,让我们回顾文章开头的问题:复杂性为何随着演化而增加?以上的讨论提出了一个可能的答案:复杂化的过程就是生命可占据的新状态空间逐渐增加的过程,其中的每一步都在改进生命自我复制和延续的能力,但与此同时,也打开了熵增的新通道。
复杂化不是一个单行道——正如过往数目众多的物种灭绝所示,复杂化是一个纯粹的统计学过程,可增可减。之所以复杂性看起来只增不减,只是因为生命起源于低复杂性的状态中,因此在统计学意义上,早期演化中可能实现的更复杂的状态比更简单的状态要多,因此复杂性更可能增,而非减。
但与熵不同,无尽的复杂化绝非必然。在任一时刻,随着生命的复杂性增加,通往新的状态空间泡泡的通道也会打开——其中的一些泡泡小而没有出口。一个例子就是核武器的发明:在这里,小而没有出口的泡泡象征着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末日。生命越复杂,通往泡泡的通道就越多,没有出口的的泡泡也就越有可能被发现。
而熵就不一样了。熵它什么也不在乎。熵它不会减少一分一毫。
Box 1 主要的时空演化节点
核酸
这些分子能进行序列复制,由此使更成功(能持续更久)的序列延续下来,从而大大增加了化学反应的作用时间。
ATP
这个分子能够储存并再分配能量,从而允许化学反应覆盖更长的时间的更大的空间。通过与核酸的协作,ATP 与复制和延续的过程相融合,同时也增强了这些过程。
光合作用
调节光合作用的化学反应使得太阳释放的自由能可以被大量采集,并用于驱动那些支持着自我复制的过程。
细胞膜和细胞微管
细胞膜将自我复制的过程从外界环境中保护起来;细胞微管则一方面允许细胞内的能量和材料移动,另一方面允许细胞本身进行运动。
基因-基因相互作用和同源盒(homeobox)基因
随着核酸序列开始调控其他序列,表现型的数量(可到达的状态空间的大小)大大增加,并为发展序列(developmental sequencing)和复杂多细胞生命的起源做出了铺垫。
神经元和突触可塑性
神经元允许了多细胞生物体内的信息进行快速传播,从而发展出复杂的适应性行为。而突触可塑性则让神经元的影响覆盖了更长的时程,使生物能用过去的事件来预测(并适应)未来。
肌肉细胞和机动性
在物理空间内进行远距离移动的能力,极大地改进了生物获取能量的方式,但也同时推动了猎食的演化。猎食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压力(selection pressure),并可能是寒武纪大爆发(Cambrian Explosion)时,复杂生命体种类急剧增多的原因之一。
大脑与空间表征
随着神经系统获得对外部世界形成内在表征的能力,这些内在表征大大增进了动物适应和预测环境的能力。动物从此能记住食物、水、遮蔽、同类等等的位置,也能建立可返回的固定营地。
语言
个体的想法被空间和时间隔开,而语言则允许人类超越这些间隔,从而发展出新的行为和技术。与核酸一样,语言使得信息的储存跨越时间。
基因之外——技术
人类借助语言发展出了技术,技术则增进了我们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存在,允许我们做到许多以前无法做到的事情。这使得地球这颗行星面目一新,并到达了一个全新的地理学纪元——人类世。
重要问题
人类可以防止自己的灭绝吗?
作为(很可能是)第一个能理解并预测其经历的物种,我们很容易认为自己能预防灭绝。然而,本文中提到的熵增过程,是描述物质和能量的一个基本热力学性质——因此,灭绝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更合适的问题应该是,我们是否能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延续下去?要达成这个目标,我们需要避免由我们当前的复杂性而带来的灭绝途径,包括战争、疾病和自动武器等致命技术。
人类是否会控制自己的演化?
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过去,演化是如何驱动复杂化的。然而,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演化就在同人类的技术进步并肩前进。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人类开始修改不同生物(可能包括人类自己)的基因组,这两股力量将会融为一体。基因编辑技术(如 CRISPR)是否会取代演化,成为复杂化的驱动引擎呢?我们人类会不会利用技术来驱动自己大脑的演化呢?这样做势必会打开通往更多状态空间内的泡泡的通道。我们是否能选择进入哪个通道,从而避免灭绝呢?或者,也许我们的技术进步会将人类更快地推向灭绝?
参考文献
Dodd, M.S. et al. (2017) Evidence for early life in Earth’s oldest hydrothermal vent precipitates. Nature 543, 60–64.
Jeffery, K.J. et al. (2020) On the statistical mechanics of life: Schrödinger revisited. Entropy 21.
Murthy, K.P.N. (2006) Ludwig Boltzmann, Transport Equation and the Second law.arXiv Prepr. cond-mat/0601566.
Schrödinger, E. (1944) What is life? The physical aspect of the living cell and mi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Szathmary, E. and Maynard Smith, J. (1995) The major evolutionary transitions.Nature 374, 227–232.
Wachowius, F. et al. (2017) Nucleic acids: Function and potential for abiogenesis. Q.Rev. Biophys. 50, 1–37.
Gould, S.B. (2018) Membranes and evolution. Curr. Biol. 28, R381–R385.
Plattner, H. and Verkhratsky, A. (2016) Inseparable tandem: Evolution chooses ATP and Ca2+ to control life, death and cellular signalling. Philos. Trans. R. Soc. B Biol. Sci. 371.
Shih, P.M. (2015) Photosynthesis and early Earth. Curr. Biol. 25, R855–R859.
Emes, R.D. and Grant, S.G.N. (2012) Evolution of synaps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Annu. Rev. Neurosci. 35, 111–131.
Mitchell, D.R. (2007) The evolution of eukaryotic cilia and flagella as motile and sensory organelles. Adv. Exp. Med. Biol. 607, 130–140.
Libby, E. and B Rainey, P. (2013)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multicellularity. Phys. Biol. 10.
Holland, P.W.H. (2013) Evolution of homeobox genes. Wiley Interdiscip. Rev. Dev. Biol. 2, 31–45.
Kristan, W.B. (2016) Early evolution of neurons. Curr. Biol. 26, R949–R954.
Evans, S.D. et al. (2019) Slime travelers: Early evidence of animal mobility and feeding in an organic mat world. Geobiology 17, 490–509.
Marshall, C.R. (2006) Explaining the Cambrian “explosion” of animals. Annu. Rev.Earth Planet. Sci. 34, 355–384.
Cavalier-Smith, T. (2017) Origin of animal multicellularity: Precursors, causes, consequences—the choanoflagellate/sponge transition, neurogenesis and the Cambrian explosion. Philos. Trans. R. Soc. B Biol. Sci. 372.
Bengtson, S. (2002) Origins and early evolution of predation. Paleontol. Soc. Pap. 8, 290–317.
Bengtson, S. and Zhao, Y. (1992) Predatorial borings in late Precambrian mineralized exoskeletons. Science (80-. ). 257, 367–369.
Ma, X. et al. (2012) Complex brain and optic lobes in an early Cambrian arthropod.Nature 490, 258–261.
Ryan, T.J. and Grant, S.G.N. (2009)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synapses. Nat. Rev.Neurosci. 10, 701–712.
Martin, S.J. et al. Synaptic plasticity and memory: an evaluation of the hypothesis. , Annu Rev Neurosci, 23. (2000) , 649–711.
Wiener, J.M. et al. (2011) Animal navigation: A synthesis. Anim. Think. Contemp. Issues Comp. Cogn. 8, 265.
Seelig, J.D. and Jayaraman, V. (2015) Neural dynamics for landmark orientation and angular path integration. Nature 521, 186–191.
Hafting, T. et al. Microstructure of a spatial map in the entorhinal cortex. , Nature, 436. (2005) , 801–806.
Jeffery, K.J. and Burgess, N. (2006) A metric for the cognitive map - found at last? Trends Cogn Sci. 10, 1–3.
Kim, I.S. and Dickinson, M.H. (2017) Idiothetic path integration in the fruit fly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Curr. Biol. 27, 2227-2238.e3.
Mittelstaedt, M.-L. and Mittelstaedt, H. (1980) Homing by path integration in a mammal. Naturwissenschaften 67, 566–567.
Wang, R.F. (2016) Building a cognitive map by assembling multiple path integration systems. Psychon. Bull. Rev. 23, 692–702.
O’Keefe, J. and Nadel, L. (1978) The Hippocampus as a Cognitive Map, Clarendon Press.
Eichenbaum, H. (2014) Time cells in the hippocampus: a new dimension for mapping memories. Nat. Rev. Neurosci. 15, 732.
O’Keefe, J. et al. (1998) Place cells, navigational accuracy, and the human hippocampus. Philos. Trans. R. Soc. B Biol. Sci. 353.
Hassabis, D. et al. Patients with hippocampal amnesia cannot imagine new experiences. , Proc.Natl.Acad.Sci U.S.A, 104. 1726–1731.
Hassabis, D. et al. (2007) Using imagination to understand the neural basis of episodic memory. J. Neurosci. 27, 14365–74.
Arbib, M.A. (2005) From monkey-like action recognition to human language: An evolutionary framework for neurolinguistics. Behav. Brain Sci. 28, 105–124.
Moorjani, P. et al. (2016) Variation in the molecular clock of primates.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113, 10607–10612.
Falk, D. (2016) Evolution of brain and culture: The neurological and cognitive journey from Australopithecus to Albert Einstein. J. Anthropol. Sci. 94, 99–111.
Nunn, N. and Qian, N. (2010) The Columbian Exchange : A history of disease, food, and ideas. J. Econ. Perspect. 24, 163–188.
Carrington, D. (2016) The Anthropocene epoch: scientists declare dawn of human-influenced age. Guard. 29.
dos Santos, W.D. (2019) The entropic and symbolic components of information.BioSystems 182, 17–20.
Aaronson, S. et al. (2014) Quantify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plexity in closed systems: the coffee automaton. arXiv 1405.6903v.
编译:山鸡,阿莫東森
审校:汉那,阿莫東森
封面:由©Moon 皓玥为神经现实设计
排版:酸酸,EON